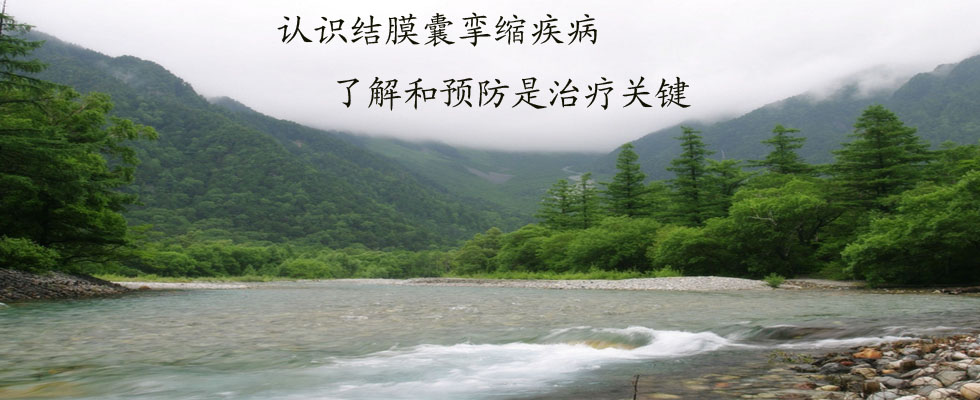大家好,我是一二三。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首诗告诉我们每一粒粮食都要重视,因为它们皆来之不易。
可实际生活中,你们是否有认识到粮食的重要性呢?
你们可曾想过这样一个画面:
当你走进超市,竟然看不到任何的粮食,而你想要网购,依然被告知无法购买任何米面的时候,你是否会感到紧张呢?
平日里点点手指就可以买到自己想吃的东西,但有一天,你却被告知,没有食物了,你会有怎样的想法呢?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无比惨痛却又真实发生的故事。
希望能给曾经浪费粮食的你们,敲响一下警钟。
圣婴
大约两百年前,东太平洋赤道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反常现象,海域的水温会明显升高,沿海地区的鱼群神秘消失,海鸟也会随之大量死亡。
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气候也会变得诡异起来,飓风海啸,暴雨洪涝,高温干旱,极寒暴雪等极端现象频现。
人们称这种反常的自然现象为“厄尔尼诺”。
“厄尔尼诺”是西班牙语的译音,意为“圣婴”、“神童”或“圣明之子”。
东太平洋赤道区的居民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圣婴”,会给东方的一个神秘古国带来怎样的灾难。
公元年,年仅4岁的光绪,刚刚被扶上皇帝宝座,此时太平天国被镇压,清政府和洋人之间暂时和平,清帝国难得获得了片刻的平静。
但这平静中蕴含着“危机”。
清帝国并没有完全从两次鸦片战争的余波之中走出来,尽管清政府一再下令禁烟,但是全国范围内有很多农民出于贪婪依然顶风犯案,大规模地种植罂粟花以制备鸦片。
他们种植鸦片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贩毒的利润比种地高。
而大片土地被用来种植罂粟后,就会出现一个现实问题:使得本来就紧张的粮食贮备更加紧张。
这就为之后的浩劫,埋下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伏笔。
“圣婴”登场了,厄尔尼诺现象让中国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华北地区包括山西、河南、直隶(今河北)的降雨突然减少,土地也变得干旱。
文献显示,已经有零星地区出现了粮食歉收的情况,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引起清政府足够的重视。
接着来到了年,出现了严重的南涝北旱的情况。
南方各省出现了大暴雨,农作物损失惨重。
而北方,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受干旱影响,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等农作物全面歉收,产量减半,山东收成甚至不及往年的三成。
随后又遭遇了蝗灾,蝗虫覆盖了直隶省大部分地区,包括天津在内。
蝗灾的可怕是未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的。
蝗灾
现在估计朋友们已经鲜有机会见识真正的蝗灾,对于蝗虫,可能更多的印象是,成为夏日烧烤界的一种美食。
肉串、烤蝗虫、配上啤酒.......啧啧啧!感觉不错!
但在过去,蝗灾却是很多人无法抹去的一段灰色记忆。
蝗灾是指大量的蝗虫会吞食禾田,使农产品完全遭到破坏,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以致因粮食短缺而发生饥荒,而蝗灾往往伴随着旱灾而发生,这也是“久旱必有蝗”说法的由来。
在旱灾的前提上,再加上蝗灾的严重危害,因此而引发的饥荒等会更为严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传统的农耕经济国家,在创造了五千年辉煌历史文明的同时,也饱受着各种自然灾害和病虫灾害的侵扰。
蝗灾作为仅次于水灾、旱灾而排在第三位,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伤害的自然灾害之一,自古以来备受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重视。
当时的画面到底是怎样的呢?
八个字形容:遮天蔽日、寸草不剩。
在中国古书上就有“旱极而蝗”的相关记载,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有对蝗灾的相关记载:
“去其螟螣(mingte,害虫),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所著《除蝗疏》中,对于蝗灾造成的巨大危害有过较为明确的定位:
“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陂,水旱为灾,尚有幸免,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灾”。
发展到清朝,因为历史文献和相关书籍的详细记载,蝗灾显得尤为严重。《清史稿?志十五?灾异一》中详细记载了清朝时期蝗灾的发生情况:
顺治年间共有8年发生蝗灾,涉及60余县次,平均每2年1次;康熙27年记录个县次发生蝗灾;雍正年间,关于蝗灾的记录稍少,3年13县受灾;乾隆年间发生的蝗灾有27年,县次受灾,平均为2年多1次;嘉庆年间,3年19县次。从顺治到光绪的年中,共有91年出现蝗灾,平均约3年1次。
这场干旱让原本并不肥沃的土地更显贫瘠,而蝗灾的出现,则是热锅中的一瓢开水。
干旱加蝗灾,导致山西的一些地区,已经有人开始靠吃树皮活命。
吃树皮
下边我们来看一下老照片:
成排树木的树皮被饥荒受害者剥离吃掉,场面是不是很触目惊心?
一排排的小树树皮都被剥离了,可是已经没有粮食可吃的百姓们为了填饱肚子已经别无他法了。
事实上,大家也不是拿起树皮就啃,通常是饿昏头的人才会去这么干。
一般人们会先去扒树叶,树叶吃光了,才开始吃树皮。
树皮也是先去掉老皮,然后处理嫩皮,把它们晒干磨成粉末,再拌着野菜叶子一起吃。
当然也不是所有树皮都能吃,比如杨树皮,杨树皮吃下去非常难以消化,会让人十分痛苦。
一般来说,饥荒时人们所食用的树皮就是指榆树皮。
榆树皮富含人体必需的碳水化合物和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高;可食用部分无异味,又有黏性,加工成面食后口感Q弹有嚼劲,至今陕西地区仍有做榆树面的风俗。
最关键的,大自然中很多树皮都有毒,而榆树皮的安全无毒已经经过劳动人民几千年的实践检验,除了对消化系统有轻微影响外,无任何其他毒副作用,是灾荒年景中挽救了无数生命的不可多得的经过实践检验的风味美食,说它是我们的母亲树皮也不为过。
但,树皮被吃完了,灾荒依然没有结束。
而那些以为熬过今年,等明年就能吃上饭的灾民,做梦也不会想到,在未来的两年,连树皮都成了奢侈物。
恐怖开始
年,光绪三年,连续大旱第二年,大饥荒正式拉开序幕。
这一年,特大旱情并没有丝毫缓解,而蝗灾却再度来袭。
其中山西各地迎来了全面旱荒,粮食大面积绝收。中国的老百姓对于灾荒是非常敏感的,一些有逃荒经验的民众知道,如果留下来,对于他们来说只怕是九死一生。
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清廷奏报时称:“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jìn)奇灾,古所未见”,“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面对如此强悍的旱灾和蝗灾,清政府显得“很无力”。
一方面虽然李鸿章等官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但清政府官场腐败严重,导致大量水利设施形同虚设。
另一方面便是脆弱的储粮体系根本经不住如此严酷的考验。
这里需要说一下,中国古代赈灾主要靠当地仓储和国家调拨,仓储主要有三种方式:常平仓、社仓和义仓,其中最重要的是常平仓,规模最大也最普遍,属于由政府完全控制的官仓,有稳定粮食市场的功能,谷贱时增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遇到灾荒年月,常平仓又能发挥救灾功能。
那时的山西,是一个四面环山道路崎岖的内陆省份,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很难适宜粮食长途贸易,要保证粮食安全,唯有重视仓储才是唯一出路,可惜,在清朝末期,朝政腐败,本该保证足够仓储的常平仓却形同虚设。
平时根本无法储备足够的粮食,这样就导致了千百年来最为关键的国家储备粮食制度在灾难面前束手无策。
还有一点很重要,山西和陕西两省恶劣的交通条件。
朝廷调拨的10万石救灾粮,还有民间采购的赈灾粮,都必须穿越重重山路才能入晋。入晋之后,大半还是崎岖的山路,不得不靠牲畜驮运或是手推小车运送,还有的是人背肩挑。
恶劣的交通条件导致国家筹集的上千万两赈灾银只有少部分用于购粮,而大部分充作了运费。高昂的运费还在其次,更致命的是大量的赈灾粮由于极其恶劣的交通条件,根本无法及时运抵遭受饥荒的地区。
朝廷给山西调拨的赈灾粮,从光绪三年夏天调拨后,直到光绪四年春才有少量运到,大批的赈灾粮运到灾区则是当年冬天的事了,此时饥民已大批冻饿而亡。
没有水利、粮仓无粮、赈灾粮又进不来,灾民只有一条路可走:逃难。
当地知府得知老百姓要逃荒,立即赶赴现场,苦苦哀求百姓不要离开家乡,并且承诺一定会赈济百姓,老百姓见状,哗啦一下跪倒一片,说:“多费府大老爷好心,念我们饥寒,就是每家与我们三两斗麦子,能吃几日?”
老百姓知道,现在趁还有体力,能跑赶紧跑,要是跑到了有收成的地界说不定还能捡条命,要是留下来就真的死定了。说完大家叩头,哭声一片,知府也嚎啕大哭起来,官民就这样相对痛哭,可是哭也没用,老百姓依然逃散一空。
恐惧在华北各地蔓延,逃荒大潮已经势不可挡,有的官员因为无力阻止百姓逃难,绝望之下悬梁自尽。对于当时华北地区的人民来说,末日的帷幕才刚刚拉开。
严重旱情依然在继续,有的土地已经旱得冒起了黄烟。
当时在山西,饥民为了活命,树皮草根都已吃光,绝望的民众还能吃什么呢?
答案是……吃土。
饿到吃土
吃土,现在成了一句网络用词,指穷到没钱吃饭只能吃土,后来引申到网络购物时,强调购物的疯狂程度,网友们常在过度购物时自嘲花销太大下个月“吃土”。
谁能想到,那个时候为了生存,真的有人在吃土!
人们把草根树皮吃之后又去吃随处可见的石头,把石头砸成小石子,磨成石粉混进面粉里吞下。
可是石头毕竟是石头,即使磨得再细也有棱角,有的人就被石子划破肠胃而死,有的人因为消化不了石子,又排泄不出被憋死。
农村还有一种黏土叫“观音土”。
什么是观音土?观音土本质上属于黏土矿物,就是一种高岭土,是用来烧制瓷器和釉料的重要原料。
全国不同地方对观音土的称呼不尽相同,白泥、灶土、甘土等都是观音土的别称。观音土中含有多种矿物成分,具有稳定的化学成分,素有“万能石”之称。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观音土的众多矿物成分中,含有很多金属元素,即铝、镁和锌等,显然,它并不是真的食物。
但是,在农村那个生存都极其困难的饥荒年代,大家为了果腹保命,观音土就成了救命粮,谁还管它有没有害处,只要吃了能填饱肚子就行,饥不择食的村民纷纷寻找观音土,挖来充饥食用。
而实际上,观音土的口感也并不是美味可口,而是尝起来有一种浓重的土腥味,十分咸涩难咽,但是那时几乎饿成“疯魔”一般的人们,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任何能用来的填饱肚子的东西在他们眼中都是珍贵绝顶的“美味”。
为了更好地享用这些观音土,有些讲究的人都会处理一下再加以食用,而所谓的处理,就是把观音土晒干后敲成细细的如面粉一般的粉面,然后拌上些许细糠做成饼子来当做填饱肚子的美食。
那时有人说,“三斤面,七斤神仙土,吃了就没问题”,事实证明,这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罢了,历史上因为吃观音土而殒命的饥民数不胜数。
因为观音土本身是没有什么营养的,这玩意说到底就是土而已,它即使被人们吃进肠胃中,也不能被吸收或消化,它只能给人一种饱胀之感。
唯一的优点便是可以短暂缓解人们肠胃因饥饿难耐而所忍受的痛苦。
少量食用观音土还可以,但是如果过度食用,就会让大量观音土堆积人的胃中,坠得人的肠胃疼,还会破坏人们的正常排便功能,使人活活憋死。
但即使这样,在那个饥荒盛行,生命如此脆弱的年代,反正早晚都会死,所以大家宁愿做饱死鬼也不愿做饿死鬼,还是照样食用观音土来充饥。因此观音土又被人称为“最绝望的食物”。
吃人惨案
当时在灾区的一些地方,谣言四起,说老百姓要饿死了,可是当地的一些大户人家家里有粮,一些灾民就开始砸大户人家院门要粮,可是灾情都到这地步了,地主家也不可能开门。
地主知道,粮食就这么多,一旦分出去自己就会饿死。
那些大户人家就闭门不答,外边的灾民先是叫骂,发现没效果之后,他们想一个招,当时满大街都是死人,那些灾民就拖来很多尸体,先把尸体吊在大户人家的院门前边,然后再把死人脑袋给剁下来然后扔大户人家院里,就用这种方式勒索粮食。
在这时候还有人能有劲扔人脑袋,可是随着灾情的进一步加重,就连这种勒索粮食的无赖行为都消失了,弥漫在灾区的恐怖又深入了一层。
接着,有人为了活命,开始吃人。
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
吃人肉、卖人肉者,比比皆是。
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老人或孩子活杀吃的……无情的旱魔,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根据一位清朝人回忆灾荒的书《晋灾泪尽图》,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位来自南方的客人,路过山西的时候正好赶上这场灾荒,自己的老婆被活活饿死了,他忍不住嚎啕大哭,但是他身边的人立即把院门关上然后让他闭嘴,因为当时在街上已经有了抢尸而食的事发生,只要有人一哭,就有人知道这院子里死人了,马上就会有人来抢尸体吃。
那个死了老婆的人就问说那怎么办,身边的人说等到了夜里,咱们再把你老婆埋院子里让她入土为安,当天夜里,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尸体埋在院子里,生怕惊动抢尸人,等第二天天亮了他们再到院子里一看,院子里的尸体已经被人挖出来吃的只剩骨头了。
这种事还不是个例,在山西各地接连出现,说有一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夜里睡觉的时候听见院子里有动静,主人就从窗户缝望出去,发现月光之下有两个人背起他母亲的尸体往外跑,那主人赶紧追出去,一直追到了那两个人的住所,但是那屋主人发现那两个人手里拎着斧头和砍刀,就不敢进去,只好赶紧跑回村子找人帮忙,等一大群主持公道的村民回到现场时,发现屋主母亲的尸体已经被扒光了放在大锅里煮熟了。
村民们一哄而上,把那两个凶手五花大绑抓起来,整个过程中,那两个凶手一直大声叫骂:“宁为村中死鬼,不为县中活人!”村民捆巴那两人的时候一抬头,傻眼了,发现在那两个人的屋子里全是死人骨头,这两个人已经饿疯了,变成了食人魔,不知道他们吃了村子里多少人。最后村民协商,把这两人用铡刀活活劈成了两半。
一旦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就标志着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同时那些吃人的灾民难道就可以真的幸免于难吗?
答案是否定的。
吃人肉很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库鲁症。
库鲁病是最早被研究的人类朊毒体病,曾经仅见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高地有食用已故亲人脏器习俗的土著部落,自从这一习俗被废止后已无新发病例。
库鲁病潜伏期长,自4—30年不等,起病隐匿,前驱期患者仅感头痛及关节疼痛,继之出现共济失调、震颤、不自主运动,后者包括舞蹈症、肌阵挛等,在病程晚期出现进行性加重的痴呆,神经异常。先后有震颤及共济失调后有痴呆是本病的临床特征。患者多在起病3~6个月内死亡。
行尸走肉
时间来到年。
此时这场从年开始的大旱,已经持续了三年,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干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缓解;到6月间有过短暂的雨水期,之后又连续亢旱,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
不过从整个灾区来看,旱情开始减轻,陕西、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旱情都趋于缓解。
但是,经过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老百姓对于灾害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极限,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并未因旱情的缓解而相应地减少,反而更多更严重了。
在山西.越来越多的村庄和家庭毁灭于灾难之中。在河南,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即为饿犬残食。
大部分尸体因为迅速腐败,人类已经不能食用了,但是对于食腐的狼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美味,腐烂的尸体吸引了大量野狼进入人类活动的地方,以至于灾区出现了野狼吃人的狼灾。
狼群在灾区各地四处游荡捕食百姓,任何与它们遭遇的人都留不下全尸。
河南境内,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连割人肉的力气都没有了。
无数面如僵尸的灾民摇摇晃晃地走着,野狗则跟在这些灾民身后,一阵风吹来就能吹倒几个难民,倒地的人还没咽气就已经被扑上来的野狗分食。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时候倒死在地上。
春夏之交,北方大部又因灾害引发了瘟疫,河南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灾后继以疫疠,道殣相望”,山西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有的外国传教士实在饿的受不了了,就想找一户人家要点吃的,于是传教士就走进一间民宅讨饭,刚一进屋差点滑一大跟头。
他低头一看,地上一层蛆,因为这家人全家都饿死在了屋里,没人给他们收尸,全家烂在屋里,尸体上的蛆已经堆不下了,苍蝇没地方下新的蛆,所以新蛆只能噼里啪啦地从尸体流淌到地上,这个传教士几乎被吓疯了,夺门而逃,从此再也不敢随便进入灾区任何一家民宅。
有一个曾经去过灾区的人回忆了这样的场面:
他们路过灾区的时候就听自己这马车在行进的时候”咔嚓咔嚓“直响,他探出头一看,发现路上全是累累白骨,那咔嚓声是车轮碾碎死人骨头的声音。这人吓得缩在车里瑟瑟发抖不敢再看,没想到过了一会,刮风了,大风吹进车里很多黑色的毛发,吹的那人脸上身上都是,那人摘干净仔细一看,吓得差点尿裤子里,他发现那些毛发全是死人的头发,有的头发还能辨认出死者生前的发型,当时的灾区,饿殍遍野,那些荒野上的尸体的头皮已经被喜鹊和乌鸦啄烂了,死尸的头发被大风吹遍原野,于是山西大地上吹起黑色的风。。。就这样,灾民们曾经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证据也在风中吹散了。。。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经这么评价这次灾荒:
“就是地狱也不过如此了。”
李提摩太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于年初进入受灾最重的山西,他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保存了一些当年的日记片断,读来触目惊心。
在受灾最重的山西南部地区,李提摩太“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
“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晨,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赈灾,在两种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
据李提摩太所记,他初至太原拜访曾国荃即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曾的秘书告诉他,巡抚因为李提摩太的出现而非常生气。
李提摩太写道:“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两千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办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依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然而曾国荃毕竟不是死读圣贤书的腐儒,当其意识到李提摩太一行并无恶意时,很快改变了态度。
当李提摩太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曾国荃给其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辞的信,而为李提摩太蒙在鼓里的,是曾国荃奉命调查他而上的一道奏疏。
曾国荃说:“此次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等,携银来晋放赈,迭准直隶来咨,当即分委妥员会同办理,先在阳曲徐沟,诸称平顺。嗣该教士闻省南灾务尤重,愿赴平阳散放,亦经分饬照料办理,均极妥协,并无河南所奏情事。”
曾国荃与洋教士的诚恳交往,对山西赈灾意义重大。
李提摩太自带银两不多,但他通过日记等形式向海外通报灾情,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据统计,经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赈者从饥馑线上挽救过来的家庭数目达到十万户,得到救济的人员高达25万人。外洋赈款20余万两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负责发放了12万两,领赈灾民超过15万人。
奇荒尾声
进入年,光绪五年,尽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东起直鲁、西迄陕甘的广阔土地上,毕竟已降下甘霖,乾涸的河床里重新荡漾起清波,龟裂的土地开始滋润,并重新泛起了绿意。
旱灾已进入尾声,苦难的岁月就要结束。
可是,正当死里逃生的人们准备重建家园之时,一场新的灾难骤然而至,这就是7月1日发生在甘肃武都的震级达8级、烈度为11度的大地震。在地震中受到破坏或受到影响的地区,大部分在旱灾区域之内。
………
从年到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
大旱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饿殍载途,白骨盈野”,受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民众人数,多达1.6亿到2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
而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约万人,仅山西一省万居民中,就死亡万人。
由于这次大旱以年、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对于这次丁戊奇荒中的灾民,出现了哪些救治方法呢?
灾民主要靠有限的民间赈济,一是江南士绅,如无锡富商李金镛与江浙富商胡雪岩率先倡导发起义赈活动,自发到华北特别是山东赈灾,在山东设立江广助赈局,发放的赈灾款达到了五六十万金。赈灾的重点对象是儿童。
二是外国教会也积极赈灾,但在河南省遭到强烈抵制,传教士甚至无法在河南省立足,但传教士在山东省获得了部分成功;
三是设立粥厂,江苏巡抚吴元炳在清江设立了17个粥厂,收容四万五千余人,南京、苏州等重镇也都在城外设置了粥厂,地方政府官员亲自负责,甚至连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在灾荒开始的第一年收容了一千二百多人。
尽管赈灾的速度赶不上难民出现的速度,但确实有许许多多的人主动站出来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后记
“丁戊奇荒”为什么会造成上千万的人死于非命?考查一下清朝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不难发现,这场触目惊心的大灾害,既是天灾,又为人祸。
天灾自然就是连年大旱,再加上蝗灾。
这确实是丁戊奇荒的根本原因。
也许我们无法决定天灾,无法决定天气,无法阻拦蝗虫,但实际上,对于人祸,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做到尽量避免的。
首先就是粮食储存。
当然这也要归因于清政府的昏庸无能。
完善的粮食储备是一个国家能否正常运转以及在大灾面前可以挺立的重要保证。与历朝历代一样,清王朝也在各省、州、县设置了粮仓,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
但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朽,仓储制度也渐趋衰败。各级官吏非但没有及时采买仓谷,反而借机变卖、挪用、侵盗粮食。
这样一来,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粮仓不能及时对民众进行供给,都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其次,鸦片。全国各省几乎都有鸦片种植,山西、河南、山东等重灾区更是生产鸦片的重要基地。以山西为例,年,山西耕地面积约为万亩(当时全国耕地约8亿亩),其中60万亩种植了鸦片。
山西巡抚曾国荃后来曾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因为种植鸦片不仅侵占良田和劳力,造成粮食不足,而且诱使相当部分农民自种自吸食,影响了健康和劳动能力。继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也指出:“垣曲(山西运城境内)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多。”
清代末年这场特大旱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当年清朝官员提起这场旱灾,称其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
丁戊奇荒已经远去,但绝不应该被我们忘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铜为鉴,可正衣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PS:
感谢我们伟大的国家,让我们不再挨饿,树皮、草根、观音土也不再是人们用来充饥的口粮。
生活条件持续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对于食物,我们始终应该抱有一颗敬畏之心。
社会也一直在倡导“光盘行动”,可食物浪费,依然触目惊心。
这里就要说下大胃王了。
之前网络上盛行“大胃王”,出现了很多水平低下、吃相难看的男男女女,他们在各大平台的镜头前,展现自己的超乎寻常的“胃口”,为了流量和